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2017年5月4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一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1.被申请人一将拥有完全产权的豪沃牌牵引汽车出售给申请人,再由申请人将该车辆出租给被申请人一;2.租赁期限为2017年5月4日至2019年5月3日,被申请人一应在《融资租赁合同》签署后每月10日按时足额向申请人支付租金;3.被申请人一未能按时足额支付到期租金的,申请人有权立即通知被申请人一解除合同,要求被申请人一立即返还租赁物或无需经司法程序即取回或禁止被申请人一使用租赁物;4.因被申请人一违约,申请人为保障租赁物安全,收回租赁物的,不意味合同的终止或解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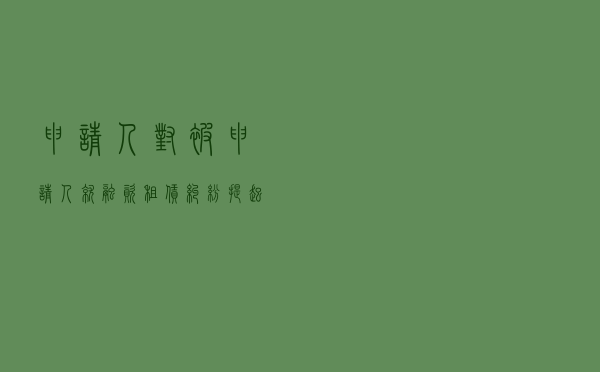
同日,申请人根据被申请人一的指示将购车款支付给车辆卖方;被申请人一向申请人出具《租赁物接收确认函》,确认收到案涉租赁物;被申请人一还向申请人出具《声明函》,被申请人一无条件同意在其出现相关违约情形时,由申请人直接采取包括收回租赁车辆进行处置的方式用于清偿其对申请人的债务。
同日,被申请人二、被申请人三、被申请人四出具《保证函》,为被申请人一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自2018年9月30日起,被申请人一未再向申请人支付租金。2018年11月20日,申请人委托案外人甲拖回案涉租赁物,并向甲支付了拖车费1万元。该次扣车之后,双方进行协商,被申请人一、被申请人二认为申请人提出的违约金及拖车费过高,最终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至申请人申请仲裁时,被申请人已经逾期9期租金未支付。
本案中,申请人提出解除《融资租赁合同》,要求被申请人一按照全部未付租金及迟延付款违约金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向申请人赔偿损失,并要求被申请人一承担收车费用等。被申请人则提出仲裁反请求,要求申请人返还租赁物并赔偿车辆停运损失等。
【争议焦点】
1.申请人是否有权自力取回租赁物并要求被申请人一承担收车费用。
融资租赁中,出租人自行取回租赁物类似于自助行为,自助行为属于私力救济。同公力救济相比,其具有便捷性、有效性的特点。且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出发,考虑到权利保留、国家特许、底线救济、个人自治、公力救济正当性危机等因素,其亦具有正当性。我国法律法规并未禁止自力取回租赁物,只是权利人自力取回租赁物的过程中不可采取暴力、胁迫等违法方式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融资租赁中出租人自行取回租赁物,还可以理解为合同赋予的一项民事权利。合同中,出租人一般都会与承租人约定,在承租人拖欠租金等违约情况出现时,出租人有权取回租赁物,该约定可理解为对违约责任的约定,即出租人可以采取自行取回租赁物的方式追究承租人的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民事权利可以依据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法律规定的事件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取得。”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 出租人自行取回租赁物的权利属于民事权利,出租人、承租人通过签订合同的民事法律行为赋予了出租人该项权利,则出租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承租人或他人不得干涉。
本案中,申请人在被申请人一违约的情形下,以自力取回的方式收回租赁车辆符合合同的约定,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强制性规定,故仲裁庭予以支持。
2.申请人收回租赁车辆后,被申请人一是否有权主张车辆停运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 因此,出租人自力取回租赁物后,应当出于减少损失的善意,及时和承租人协商处理,比如要求承租人立即履行合同、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等。在无法协商解决的情况下,应当及时采取法律措施,而不能放任双方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使损失扩大。本案申请人于2018年11月20日取回租赁物,但直到本案申请仲裁,申请人才在仲裁申请书中要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明显超出了合理的时间,具有相应的过错。在仲裁申请书送达被申请人一前,合同并未解除,被申请人一仍需履行合同义务,根据合同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被申请人一有权要求享有合同的权利,即使用租赁物,故仲裁庭酌定在租赁物被申请人取回后三个月起至合同解除前,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一车辆停运损失。
【裁决结果】
仲裁庭最终认定:《融资租赁合同》解除,被申请人一应向申请人支付相应的损失赔偿金及收车费用;申请人应向被申请人一支付相应的停运损失,并驳回被申请人要求返还租赁物的仲裁请求。
【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九条 民事权利可以依据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法律规定的事件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取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条 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
【结语和建议】
本案事实并不复杂,在车辆融资租赁业务中,出租人往往对租赁车辆装有GPS,有些还持有钥匙,这为承租人违约后,出租人自行取回租赁物提供了便利。在实践中,出租人为了减少损失,首要寻求的救济方式也是取回租赁车辆。仲裁庭在审理本案时,对第一个焦点问题,即收车费用的承担问题,其实还隐含了对出租人自力取回租赁车辆合法性的评价问题。如果对自力取回行为的合法性不予认可,则该项主张显然不能支持,只有认可自力取回租赁车辆行为的合法性,才能进一步审查合同是否有约定、支出是否合理的问题。那么,对于未征得承租人同意,出租人趁承租人不注意将租赁物予以取回的行为,是否有法律依据?该问题似乎处于法律空白地带,但仲裁庭充分考虑了承租人违约的事实、合同的约定、该行业的惯例,以及民事法律对当事人维护自身权益方式的精神,对出租人自力取回租赁物的行为予以认可,进而根据合同的明确约定,支持取回费用由承租人承担。
其次,对取回后的停运损失,承租人是否有权向出租人索赔?在出租人取回租赁物后,双方的心态往往会发生变化,对承租人而言,既然租赁车辆已被取回,则自然会认为无需再支付租金,但对出租人而言,处置租赁物后如果不足以弥补损失,则承租人还需继续承担租金,如果在车辆价值能基本弥补出租人损失的情况下,出租人有时便不急于处置。但此处其实涉及到时间价值的评判,如果取回租赁物后不快速处理,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租赁物价值可能贬损,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未还租金产生新的违约金或逾期利息,将加大承租人的偿还责任。但本案的焦点为租赁物取回后的停运损失,从合同的角度,合同明确约定了承租人违约的情况下出租人有权取回,似乎由此造成的后果或损失都应由承租人承担。但事实上,如果出租人在取回租赁物后的合理时间内就双方的合同关系进行处置,则可以及时止损,而如果出租人取回租赁物后,不对双方合同关系及时进行处置,对承租人而言实际是不公平的,因为,一方面合同尚未解除,其仍应根据合同约定承担继续扩大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租赁物被取回,其又无法享有合同的权益。由此,仲裁庭适当支持承租方的停运损失,实际是对双方责任的明确、权利义务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