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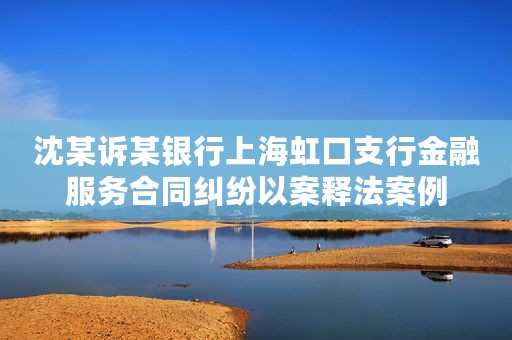
原告沈某自2014年5月起在被告某银行上海虹口支行处购买理财产品。2015年5月8日,原告购买了被告代销的申万菱信申万电子行业投资指数分级基金,认购金额50万元。2016年1月20日,原告所购基金下折强行平仓179,475.30元,后通过了解得知所购基金为分级基金,并非是自己原以为的常规基金,认为被告欺骗销售。2016年3月3日,原告赎回所购基金,余额仅为273,680.79元,亏损226,319.21元。现起诉至法院,请求: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226,319.21元(币种下同);二、判令被告赔付原告自2015年5月8日至今以50万元本金为基数的利息(按当年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利息计算)。
【调查与处理】
2017年7月31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被告某银行上海虹口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沈某损失10万元; 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判决后,原告沈某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2017年10月31日,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律分析】
原告在被告处开设账户,长期在被告处投资购买理财产品,借助被告银行客户经理的推介服务完成相关交易。被告银行向原告提供金融方面的专业化服务,银行与客户之间构成以理财顾问服务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服务法律关系。金融服务法律关系中,金融机构在代销金融产品、提供金融服务的过程中,因双方信息不对称以及金融投资行为的专业性,自然人投资者并不具有相应专业判断和风险识别能力,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提供服务方应负有履行金融消费者适当性审查、信息披露及风险揭示的义务,通过服务实现信息对称,使投资者作出正确判断,以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一审的争议焦点如下:
(一)原告是否属于适格投资者。《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七条)、《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代理销售业务的通知》(第三条、第二十五条)均要求商业银行开展代销业务时,应当了解和评估客户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充分揭示代销产品风险,向客户销售与其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金融产品。本案原告在开立交易账户时进行了风险评估测试,评估结果为激进型客户,可以购买高风险及以下风险的理财产品。原告答辩意见中虽对风险测评报告有异议,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相关事实,且原告作为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具备长期金融理财经验的成熟投资者,应该仔细阅读审慎签署,对于自己签名确认的评估内容视为已接受认可。另外,原告签名确认的《业务申请表》《风险揭示书》均对其作为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等级进行了提示,原告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应承担签名确认后的相关法律后果。至于原告认为,凡首次购买基金产品均需另行做专门的风险测试评估,系自身误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所作的风险评估测试在购买讼争基金时未超过一年的有效期间,评估结果与讼争基金的风险程度相匹配,故本院认为原告属于适格投资者,被告未违反投资者适当性原则。
(二)被告是否尽到了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的义务。根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条款规定,均要求银行向客户明确告知产品的相关信息、解释相关投资工具的运作市场及方式,揭示相关风险,由客户自主作出选择。《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亦要求给予普通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等方面特别保护。本案讼争基金系分级基金,属于高风险等级理财产品,银行在主动推介后应当同时履行特别的提示注意义务,告知特别的风险点。被告辩称客户经理在介绍推荐讼争基金时详细介绍了讼争基金并提示过相关风险,但提供的录音录像只能证明推荐过程中提到基金风险,并未详细介绍讼争分级基金的运作方式等相关信息并揭示特别的风险点。原告此前在被告处无投资购买基金的经验,被告客户经理对此熟知,理应更为充分、全面披露相关信息,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被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尽到了讼争基金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的义务。对此,被告需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
综上,原告的风险承受能力与讼争基金风险等级相匹配,属于适格投资者,应独立承担金融投资风险。但被告在向原告推介讼争基金时未尽到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的义务,具有相当过错。若被告事先充分揭示告知分级基金的风险,则可以保障原告知情权、选择权和止损权。讼争基金的赎回最终由原告自主完成,虽然时间节点不同会造成损失数额的差异,但被告对赎回后的亏损金额予以认可。本院综合原、被告双方各自的过错责任程度和市场风险,酌情认定被告应当赔偿原告损失10万元。对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如下:
(一)沈某是否进行过有效的风险测试评估。沈某上诉主张,风险测评问卷上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未作过风险测试评估,一审中提交法庭的风险测评问卷不是原件。结合一审庭审笔录内容,本院认为某银行上海虹口支行就沈某进行过本案风险测评的主张完成了举证责任,沈某对此予以否认,未申请笔迹鉴定,亦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一审判决认定本案风险测评问卷上的签名系沈某本人所签并无不当。故对沈某的相关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二)某银行上海虹口支行是否履行过相关风险提示义务。某银行上海虹口支行上诉主张,根据《交易业务申请表》和录音录像等证据,其已充分揭示了讼争基金产品的风险,且沈某有炒股经验,能听懂所述内容。经查,讼争基金产品并非普通基金,而是存在下折风险特点的分级基金。现有证据仅能证明银行方在推介讼争基金产品过程中,提示过所认购基金属于高风险产品,但无法证明揭示了本案分级基金的特殊性和存在“下折”高风险的特点。对此,本院认为,沈某虽然有炒股经验,但分级基金与股票的运作机制和风险特点明显不同,银行在主动推介过程中更应当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充分必要的提示注意义务,不能仅笼统地告知投资者产品属于高风险,还应充分揭示高风险产品的特殊性和具体表现,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本案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银行方尽到相关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的义务。故对某银行上海虹口支行的相关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结合沈某、某银行虹口支行双方各自的过错责任程度和市场风险,所作出的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典型意义】
严监管是贯穿2017年金融领域的主题词,针对市场上存在的各种乱象,监管重拳接连落地。顺应金融严监管的大趋势,本案系本市首例明确商业银行在代销金融理财产品时负有消费者适格审查义务和风险披露、风险提示义务的生效判决,有力地规范了金融市场服务,在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方面具有典型意义。具体价值体现为如下几点:
(一)法官创设性就金融服务法律关系这一非典型合同类型进行认定和权利义务设定。明确金融机构提供财务分析与规划、投资建议、个人投资产品推介等专业性高的金融服务时所应负有的义务。提供服务方应负有履行金融消费者适当性审查、信息披露及风险揭示的义务,通过服务实现信息对称,使投资者作出正确判断,以实现合同目的。
(二)明确金融机构向非专业的普通投资者推介或销售金融理财产品时,有义务把适合的产品或服务以适当的方式推介或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依法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培育理性的金融消费意识,明确投资者个人亦负有审慎注意、风险自负和理性投资的义务,防止消费者产生非理性“亏损托底”预期。
(四)对于销售高风险金融理财产品,明确风险披露需要具备“针对性”“充分性”等要素,给予普通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等方面特别保护。不能随意损害投资人基于对银行信赖所产生的利益,提供安全、到位的金融服务,防止将不适格的投资者不当地引入资本市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