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内容
【案情简介】
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申请人甲、乙为一家专门从事民间借贷业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员工,是本案的贷款方,被申请人A公司,自然人B、C、D是本案的借款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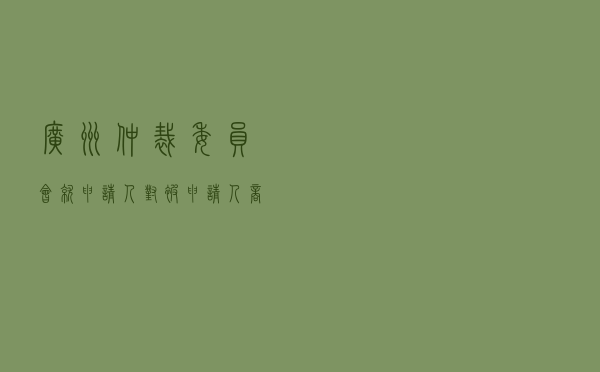
2018年5月31日,甲、乙与A公司、B、C、D签订《借款抵押合同》,约定:借款金额:1500万元。借款期限:12个月。利息利率:月利率2.5%。还款方式:借款利息从款项借出之日起计算,借款人每满一个月向出借人支付利息一次,本金应于借款期限届满之日一次性归还。
2018年6月4日,甲向C转账800万元,同日,C向甲转账381100元,向案外人丙转账30万元。
2018年6月5日,甲向C转账700万元,其后四个月C向甲转账合计150万元。A公司、B、C、D后再未向甲、乙支付任何款项。
另经仲裁庭查明:1.案外人丙为甲所在公司的员工,其收取的款项均属于甲;2.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甲作为出借人向不同的借款人发放贷款,在人民法院及本仲裁委员会的民间借贷案件共8宗(含本案),金额总计近3000万元,每笔借款的利率均超过月利率2%;3.案外人丙作为出借人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在法院及仲裁机构的民间借贷案件达10余起。
现甲、乙提起仲裁,要求A公司、B、C、D偿还借款本金,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利息。A公司、B、C、D则辩称甲、乙为“职业放贷人”,《借款抵押合同》应为无效合同。申请人预先收取利息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应从本金当中扣除预先收取的利息部分,并且认为申请人主张的利息过高,应按照不超过一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支持。
【争议焦点】
1、甲、乙是否为“职业放贷人”?
2、《借款抵押合同》的效力认定?
【裁决结果】
(一)甲、乙符合“职业放贷人”特征
通过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资金以赚取高额利息,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贷款目的具有经营性,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经常性的贷款业务,即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职业放贷”。
根据“职业放贷人”的特征,仲裁庭结合甲、乙或关联当事人在一段时间内所涉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利率、合同格式化程度、出借金额、资金来源等特征认定甲、乙是否为“职业放贷人”。经调查,本案甲在2016年至2018年期间作为出借人向不同的借款人发放贷款,在法院及本会的民间借贷案件共8宗(含本案),借款利率均超过月利率2%。另外,仲裁庭还查明案外人丙为甲的员工,并代甲收取款项,仲裁庭认为丙为甲放贷的关联人之一,且查明丙在作为出借人,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向不同的借款人进行放贷12宗的事实。据此,仲裁庭认为,甲及其关联人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多次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且利息利率均超过月利率2%,贷款目的具有明显的经营性,符合“职业放贷人”的特征。甲、乙为共同出借人,应对甲“职业放贷”的行为后果负责。
(二)《借款抵押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借款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取决于甲、乙的放贷行为是否构成“职业放贷”。结合前述认定,甲、乙符合“职业放贷人”特征。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金融该机构的业务活动”,该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故《借款抵押合同》应为无效合同。在仲裁庭已认定《借款抵押合同》无效的情况下,A公司、B、C、D应返还甲、乙出借的款项,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向其支付资金占用费,故对甲、乙要求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同时根据《合同法》第二百条之规定,预先收取的利息应当从本金当中予以扣除。
【相关法律法规解读】
《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三条规定: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业务活动。
《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三条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经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金融该机构的业务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条规定:借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
当前职业放贷高发,引发了金融监管治理和法律规制的难题,如何在法律上界定职业放贷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以上规定均涉及对“职业放贷”行为的规制。其中《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三条对“职业放贷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定性,认为“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并指明地方法院可以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
如认定为“职业放贷”行为,所形成的合同因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关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金融该机构的业务活动”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合同无效后,当事人应当返还因合同取得的财产,且应当赔偿对方因此产生的损失。本案中,因仲裁庭认定《借款抵押合同》,因此认定借款人应偿还占用的资金及赔偿资金占用费。此外,由于我国禁止“砍头息”的放贷方式,如行为人在发放贷款时预先收取利息的,收取的利息应相应在借款本金中予以扣除。
【结语和建议】
本案合同是否有效,取决于甲、乙的放贷行为是否构成“职业放贷”,即“职业放贷人”的认定问题。通过查阅相关案例资料以及结合《第九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可以总结出职业放贷一般具备如下特征:
1.以营利为目的。职业放贷人以赚取利益为目的进行放贷;
2.经常性地发放贷款。对于职业放贷人放贷的“经常性” “反复性”的认定,目前欠缺统一的立法标准,仲裁庭需要结合个案情况进行综合认定;
3.放贷对象为不特定的对象。职业放贷人的放贷对象为不特定的多数人;
4.未经批准进行放贷。根据现行的《金融许可证管理办法》,金融许可证的授予主体仅为金融机构法人与非法人分支机构。因此,就个人而言,并不能作为职业经营放贷的商事主体。
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根据同一当事人或其关联方在一段时间内所涉民间借贷案件数量、利率、合同格式化程度、出借金额、资金来源等特征来综合判断民间借贷是否构成职业放贷行为。
近年来,民间借贷发展迅速,而借民间借贷之名行“职业放贷”之实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妨碍了正常金融活动的健康发展。对此,建议如下:
一是有关机关通过构建民间借贷系统性、多层面的监管制度,在统一规范对于职业放贷行为的认定标准基础上,对职业放贷行为进行有效治理;
二是要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建立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税务机关、金融监管机关之间的协调治理机制;
三是探索建立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法院、仲裁机构之间就职业放贷人名录保持信息共享畅通;
四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加强民间借贷案件的风险甄别、预测。
五是裁判者应加强对于民间借贷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结合民间借贷的款项来源、利息利率、交易模式、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审查,查清债权债务真实情况。实质性审查民间借贷纠纷当中贷款方的“身份”。
六是对于当事人而言,应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寻求资金融通,避免落入“职业放贷”的陷阱。借款时,应当尽量了解出借人是否有职业放贷的背景资料,仔细审查借款合同约定以及留存相关债权凭证,以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






